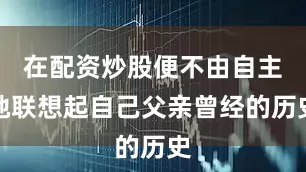
1994年,村上春树到访中国时,明确表示他绝不会触碰中国菜,坚决只吃自带的日本罐头。实际上,他对中国菜的排斥,早在得知父亲曾是“侵华暴徒”之后,便开始形成。村上将这种对中国菜的拒绝描述为一种“无法治愈的过敏症”,并坚称这与对中国或中国人民的情感无关,反而他对中国充满了浓厚兴趣。对于村上来说,这份排斥更像是一种内心深处的“父辈记忆”,每当他看到中国菜时,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己父亲曾经的历史,进而产生了生理上的强烈反应。
这种父辈的伤痛究竟是如何影响村上的呢?村上春树,无疑是当代日本文学中的巨星,他的作品广受喜爱,也成为了日本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即便村上年年竞逐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未曾获奖,但他依然在文学界和全球文化圈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不只是他的作品,村上个人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和独特的言行,也让他常常成为媒体的焦点,引发公众舆论的广泛讨论。
展开剩余81%2017年,在一本新书发布会上,村上春树冷静地表示:“日本曾在南京实施大屠杀,这一事实无可争辩,绝不应被遗忘。”这一言论让在场的日本观众震惊,并引起了轩然大波,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个人和作品的广泛批评。这场风波也让他的这本新作成为少数几本未曾获奖的作品之一。然而,当话题转到自己的父亲时,村上春树则放松心情,表达了多年来对父亲的困惑:“错,是一定错了,但罪不至死。”这是村上春树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父亲。
大学时期,村上首次发现自己的父亲曾是“侵华暴徒”,这一发现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内心挣扎。村上回忆道:“小时候,我和父亲关系非常好,他在我眼中是那样伟大。”然而,这个曾经在他眼中高大无比的父亲,随着村上对历史的了解和父亲的真实身份的揭露,变得如此陌生,甚至让他感到深深的羞愧和无助。这个内心的冲击,甚至使得他选择逃避,避开一切与父亲有关的事情。
村上春树的父亲出生于京都市,脾气古怪,但对村上异常宠爱。父亲的慈祥与耐心让年幼的村上对他充满了依赖和尊敬。每个早晨,村上的父亲都会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为村上祈福,闭眼诵经,然后解释说自己是在“超度亡灵”。然而,年幼的村上充满了好奇心,总是反复追问:“要超度的到底是谁?”每次父亲只是简短地回答:“二战中的战友,死去的中国人。”无论村上如何追问,父亲从不再深入解释。这种言简意赅的回答,让村上始终无法理解,父亲话语中的那份沉默和回避,也渐渐让村上产生了疑惑。
1955年,村上春树正式进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开始接受正式教育。父亲对村上的学习并没有过多干涉,除了对书籍的选择有一定的限制。他很支持村上对文学的兴趣,这也为村后来走上文坛奠定了基础。从小学到初中的成长过程中,村上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和历史书籍,这些阅读的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当村上得知自己父亲曾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时,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在与父亲对峙后,村上痛苦地发现,父亲不仅参与了战俘的处置,还在战争中犯下了无法抹去的暴行。这一切如晴天霹雳般击中了村上的内心,让他无法再面对父亲曾给予的那份温情。
村上春树多次在作品中描绘父亲的形象,通常这些父亲是冷漠、独断专行且沉迷于权力的象征。无论是在《奇鸟行状录》中的绵谷升,还是在《海边的卡夫卡》中父亲琼尼·沃克的暴虐行径,这些父亲身上都刻画着父辈留下的战争阴影。父辈的“记忆遗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村上的创作方向。
村上的作品《去中国的小船》是其早期最具私密感的中国题材创作之一。1980年,这篇作品首次发表于《海》杂志,三年后收录于村上春树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作为一部反映村上个人情感和历史记忆的作品,它为后来的中国情结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小说中的“我”通过回忆与中国人的接触,展现了日本战后“原罪意识”的深刻影响,而这些情感的根源,正是村上在父亲故事中所接触到的历史伤痛。
村上春树的“中国情结”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也深深根植于个人生活的经历中。尽管他从未亲自到访中国,村上的作品中却始终呈现着复杂的情感。尤其是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表达了对中国与中国人民深深的愧疚与负罪感,这些情感跨越了文学的层面,成为了两国历史记忆的交织与碰撞。
从《去中国的小船》开始,村上就一直在与这段历史进行着复杂的对话和自我释然。尽管他始终未能摆脱父辈的阴影,但他通过文字表达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对中国的深刻关注,逐渐把这种情感从文学的层面提升为对战后历史与民族认同的深刻探讨。
村上春树始终未能完全释怀自己父亲的历史,这份无法摆脱的负罪感,成了他文学创作中最具张力的主题之一。而正是这些父辈的“记忆遗产”,深深塑造了村上春树对中国的独特感情与思考。
发布于:天津市广盛网配资-散户炒股怎么加杠杆-武汉股票配资-配资门户平台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